我在5秒内失去了15000个朋友



最近全球电脑瘫痪的那一周,我的网络世界也崩溃了。“你的Facebook账号被封了,因为你的Instagram账号doantantao57444不遵守我们的规定,”我iPhone上的通知大声说道。“你还有180天的时间上诉。登录你链接的Instagram账户,对我们的决定提出上诉。”
怎么啦?谁?但是我有一本新书和一门课程需要推广!我去了我的Instagram“账户中心”,当我点击“个人资料”时,它显示除了我的Insta和Facebook会员之外,还有一个新地址——doantantao57444。那个主打色情内容的账号肯定不是我的。我吓坏了,从我的个人资料中删除了“色情黑客”(我后来这么称呼它),但这并不重要。Facebook的母公司meta仍然暂停了我的Facebook账户。
数十年来精心策划的个人资料和专业内容瞬间消失在网络中。我是那种把门双锁的人,从来没有丢过钥匙、手机、一条短信或一封电子邮件。我怎么能在五秒钟内放错15000个朋友?
在Facebook的“帮助和支持”选项卡上,我坚持说色情黑客的账户不是我的。与此同时,我的学生奥兰多向我报告说,我领导的那个很受欢迎的学生小组的页面仍然没有我作为管理员。奥兰多仍然是一个活跃的成员,他把我发邮件给他的活动传单贴了出来,但我完全被自己的小圈子拒之门外。
如果你的身体坏了,你会急匆匆地去看医生。如果你的车年久失修,你会在汽车修理店看到一个机械师。自从我在Facebook上的形象崩溃后,我直接找到了源头: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我在社交媒体上给他发信息:“我的Facebook账户被一个假的Instagram账户黑了,我的Facebook账户被取消了。我怎样才能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尽管我觉得我们都在一起,但扎克伯格并不是我的朋友、粉丝或第一个回应者。
“我被黑了,还被开除了!”我在我的其他社交网站上大肆宣传,无意中激发了大量所谓的网络侦探的信息,他们声称他们可以通过电汇或Zelle支付100到500美元来解决我的问题——令人怀疑的是,他们没有使用信用卡,因为信用卡可以保护我的交易。
“不要!我的哥哥埃里克警告说,他是一名IT人员。
突然间,我认识的许多人都在给我发短信、发即时消息和发电子邮件,告诉我他们关于诈骗、网络钓鱼计划和不公平取消的噩梦。当我读到Reddit上关于Facebook和Insta被禁、限制、停用和针对扎克伯格业务的诉讼的恐怖故事时,我的焦虑越来越大。
埃里克的同事是meta在中西部的一名员工,他主动提出帮助我,还有一名在meta纽约办公室工作的前学生也提出了帮助我的建议。从我的公寓里可以奇怪地看到meta的办公室。但这家公司并没有给我任何帮助,只是让我提交一个内部帮助单,然后等待。一周后,我收到了一封来自Facebook支持团队的电子邮件,询问我的情况,我提供了信息。
唉,他们没有回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多年来,当同事们哀叹社交媒体的罪恶——从对假新闻的沉迷到网络诈骗再到欺凌——我却为它辩护。作为一名大学写作教授的兼职,我认为这是一个神奇的职业工具,可以与我在过去25年里遇到的学生保持联系。我会转发他们发表的有影响力的文章,当他们找到支持他们的图书项目的经纪人和编辑时,我会分享我的骄傲。作为一名作家,我用它来发出邀请,参加读书会和小组讨论,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大批观众。在网上发帖对我的职业生涯至关重要,我认为自己值得获得一枚多任务奖章。
也许我对社交媒体如此热衷,是因为作为一个自称的勒德分子,我接触电脑的时间比较晚。2003年,我正在用我的黑色IBM电动打字机为我的处女作《五个伤我心的男人》(Five Men Who broken my Heart)打几章,我丈夫和兄弟们凑钱给我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作为我40岁生日的礼物。我完全不确定自己到底在做什么,于是我把每一章都保存在单独的文件里,发给了埃里克,然后他把它们放在一起。我被电脑的能力惊呆了,我把装着我手稿内容的蓝色文件夹贴上了“5Men1File”的标签。
我想象自己在写一些关于现代科技和互联网的经历的文章,包括《反社交媒体》(Anti-Social Media),关于我丈夫拒绝成为我的Facebook好友的文章,以及《我唯一的一夜情是在linkedIn上找到我的》。我在YouTube、Vimeo、Twitter/X、Zoom、WhatsApp、TikTok和Threads上玩了几次,但只在面对面的工作、会议和社交活动之间。
作为一个笨拙的孩子,我从来都不受欢迎,所以我几乎弥补了失去的时间和朋友。我达到了Facebook的5000个好友限制,获得了6000多名“追随者”,并创建了三个作者页面,为我合作撰写的书吸引不同的粉丝。当我在疫情期间转为教授在线写作课程时,我在全球范围内将我的私人学生小组增加到近2000名成员。
统治着我的小世界,我感觉自己像Facebook的皇室成员。当我转发文学代理和编辑联盟中有才华的protacimasams的作品,帮助他们的作品迅速传播时,我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做一个优秀的文学公民可以保护我免受所有消极和反对者的影响。我增加了出版技巧、自嘲式的自我推销和GoFundMe的悲剧页面,从不担心黑客会发生在我身上。我没有为广告付费,但我加入了许多作家和新闻团体,我曾经吹嘘自己可以在一分钟内接触100万人。
然后,噗。一切都消失了。

“如果一件事好得令人难以置信,那就是真的,”我父亲过去常说。
他是对的。现在,一个神经质的纽约女人对我嗤之以鼻,我每小时都在我的iPhone、笔记本电脑和我丈夫的电脑上上网,因为要离开我的数字王国而汗流浃背。在宣传我写的一本分享宽恕智慧的书时,我变成了一个混乱的愤怒球。我决心不被这个我已经熟练地主持了20年的像素化派对排除在外,我在恐慌中重新开始。我用一张新照片、更强的密码和双重身份验证创建了一个新的个人资料。我要求加入我自己的学生小组,但由于我是唯一的管理员,我无法批准我的请求——这是格劳乔·马克思(Groucho Marx)那个老笑话的一个令人发狂的转折,他说不想加入任何愿意接纳我的俱乐部。
如果你想重新加以前的联系人为好友,就会收到一条提示:“看起来你可能不认识这个人。”向你认识的人发送请求。”我绝望地试图重新联系我的母亲、兄弟、侄女和侄子——他们和我同姓——但我面对的是一个愚蠢的、充满敌意的算法,它离婚了,抛弃了我,一直拒绝我。
我对一个人的了解越深,我就越不可能请求他们的友谊,过去20年里我的许多朋友都忽略或回避我,担心我的账户被污染。丢人的是,我给他们发了DM、发了邮件、发了短信或打电话,向他们解释我可悲的困境,请求他们重新加入我的圈子。
我听到酷玩乐队那首著名的歌,关于一个曾经统治世界的人,但现在正在清扫他们曾经拥有的街道,这首歌不断在我的脑海里播放,并对歌词产生了过度的认同。前一分钟,我还“握着钥匙”,下一分钟,墙就把我围了起来,抹去了我的存在。我该如何哀悼失去的15000名网络战友?在Substack或Alignable上重建我的领域?突然戒掉?回去接受治疗?
“这教你什么?”我的心理医生过去常常在我受到创伤后烦人地问我。
我很幸运,我身份的其他部分没有被盗,没有人侵入我的网上银行账户,也没有人破坏重要的电脑文件。我就知道情况可能会更糟。事实证明,在电话和现实生活中与真正的朋友重新联系是很好的。
我仍然很自豪,因为我克服了自己的技术恐惧症倾向,拥抱了网络空间。然而,回想起来,我重读了一些研究,这些研究表明过多的屏幕时间会伤害孩子,并且发现成年人更多地依赖微型机器而不是与人互动也是不健康的。虽然我已经戒烟、戒酒和吸毒,但获得“赞”、爱心和病毒式传播对成年人和青少年来说都是上瘾的。正如我的治疗师曾经警告我的那样,“要小心所有的兴奋,因为它会让你脱离自我,你总是要回到自我。”
这是一个重要的人生教训吗?它指示我从科技天堂中解脱出来,在其他地方寻找社交和慰藉?
当然,就像一个糟糕的男朋友一样,当我意识到我可能能够接受失去并继续生活的那一刻,Facebook又回来了。在我所有的旧书都消失了10天后,它们奇迹般地重新出现了。我英勇的火枪手救了我。
我立即用新密码和更好的安全措施对我原来的Facebook和Insta账户进行了三重保护,祈祷我再也不用经历那次驱逐。
我也决定保留我最近做的备份配置文件。我立即接受了另一个我作为我的学生小组的成员,这样我就可以继续在那里发帖,以防万一,然后我让奥兰多成为这个页面的共同管理员。这感觉像是一种连接新旧的方式——就像拜登任命一位年轻的继任者一样——不知道我到底怎么花了这么长时间。
苏珊·夏皮罗(Susan Shapiro)是曼哈顿的一位写作教授,她是畅销书作家,也是她家人讨厌的书的合著者,其中包括《五个伤我心的人》(Five Men Who broken My Heart)和《美国盾牌》(American Shield)。她的回忆录《宽恕之旅》(The Forgiveness Tour)现在以平装本出版。你可以关注她的Instagram账号@profsue123。
你有一个引人注目的人吗你想在《赫芬顿邮报》上发表什么故事?在这里找到我们正在寻找的东西,并发送给我们pitch@huffpost.com。
相关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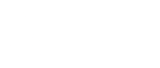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