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极端主义蔓延日

你如何决定谁拥有一个国家?今天上午10点30分在伦敦,一群黑衣男子聚集在距离英国最著名的战争纪念碑纪念碑100米的地方。他们在诵经。“我们想要回我们的国家,”其中一句重复着,接着是“你不是英国人,你不是英国人,你再也不是英国人了。”
这群人——正如他们的另一首圣歌所说——是“汤米的军队”。这指的是汤米·罗宾逊,斯蒂芬·亚克斯利-列侬的笔名,他是一名被定罪的抵押贷款诈骗犯,是一个名为“保卫英国联盟”的极右翼反穆斯林组织的前领导人。罗宾逊就在这里,在某个地方,以个人的身份出现——上周,他在被“永久封号”五年后,又回到了X(以前的Twitter)。暴力和混乱一直跟着他,所以伦敦警察厅从英国各地调集了增援部队来处理这种情况。沿着从特拉法加广场(Trafalgar Square)一直延伸到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的宽阔大道,我看到了来自英格兰北部达勒姆(Durham)和诺森比亚(Northumbria)的警车,一些警察戴着写有HEDDLU(威尔士语中警察的意思)的帽子。
警察把汤米的军队封锁在一条狭窄的人行道上,他们在那里咆哮,偶尔扔瓶子。今天是停战日,是为了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在离英国为阵亡将士默默会两分钟不到半小时的时候,我看到右翼团体冲过警戒线,突破了警戒线,然后似乎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
“你是媒体人吗?”一个女人问我,她跟着反抗者的队伍。“告诉人们警察袭击了我们。”
“那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我问。
她又看了我一眼:“你是主流媒体的吗?”
“是的。”
她对我做了个大拇指向下的手势,然后走开了。
汤米的军队在购物中心做什么?罗宾逊后来在推特上说,他和他的“退伍军人和爱国者”乐队在和平离开之前表达了他们的敬意——除了一场“小小的混战”。在我的注视下,他的一些追随者挥舞着英国国旗和圣乔治十字,但这不是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啤酒罐被丢弃在地上。一个戴着巴拉克拉瓦帽的年轻人拿着一面代表西汉姆足球队的旗帜,据我所知,这支球队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没有参战。汤米之军宣称的意图是保护纪念碑不受伦敦市中心发生的另一件事的影响——一场亲巴勒斯坦的游行从演讲者之角一直延伸到美国大使馆。但是游行要到下午才开始,而且游行路线不会经过纪念碑。
在突破警戒线后,汤米军最终远离了其成员本应保护的纪念碑。我呆在战争纪念碑旁,当纪念停战日的人群在上午10点54分安静下来时,远处的流氓们的吟唱声淹没了纪念碑上的宁静。我身边有人用伦敦东区的口音喊道:“喂,你他妈的闭嘴。”我一度怀疑,我周围的退伍军人——其中许多人戴着战斗奖章——和一个自称尊敬英国军队,但却劫持其仪式来宣扬反对移民的团体之间是否会爆发一场战斗。
当这个国家的保守党内政大臣苏拉·布雷弗曼(Suella Braverman)警告本周末将发生一场“仇恨游行”时,她并不是在谈论我刚刚目睹的场景。她指的是对以色列在加沙行动的抗议。在《伦敦时报》(London Times)的一篇文章中,她警告说,人们对抗议活动采取双重标准,但她自己对罗宾逊的示威活动保持沉默,这表明她发现一方比另一方更容易受到谴责。事实上,我今天在伦敦看到的每一次抗议——仇外的和亲巴勒斯坦的——都包含着一些令人不安的因素。总而言之,他们展示了加沙的冲突如何使英国两极分化,并助长了反犹太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
这次亲巴勒斯坦的游行是由左翼和穆斯林团体联合组织的,只是一系列有关该主题的活动中最新的一次。自10月7日哈马斯恐怖袭击和以色列随后入侵加沙以来的几周内,为反对英国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中所扮演的角色而建立的旧左翼机构又复活了。支持巴勒斯坦的激进分子包括一般的反帝国主义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批评者、和平活动家、工会会员,以及一大批大学讲师和学生。它得到了占英国人口7%的穆斯林的广泛支持。英国少数民族和左翼学者的联盟使得支持巴勒斯坦的激进主义对托米军和许多主流右翼观点专栏作家来说是如此的触发,他们认为白人左翼分子已经成为伊斯兰主义者有用的白痴,因为伊斯兰主义者和他们没有共同的价值观。
布雷弗曼更进一步,指责警方对亲巴勒斯坦抗议者过于软弱。在她的叙述中,警察——他们围捕了气候抗议者,上次我遇到他们的时候,他们把女权主义者从一名被谋杀妇女的守夜活动中拖走——对左派太同情了。
事实上,在游行前的新闻发布会上,伦敦警察厅甚至拒绝称汤米军为“极右翼”,而是坚持使用“反抗议者”这一中性词汇。他们还拒绝执行在纪念碑周围地区禁止蒙面的禁令。但布雷弗曼想要的不止这些:上周,她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批评警方不愿阻止巴勒斯坦“仇恨游行者”——用她的话说——在停战日聚集在一起。她写道:“我不相信这些游行仅仅是在为加沙寻求帮助。”“它们是某些团体——尤其是伊斯兰主义者——对至高无上地位的一种主张,我们在北爱尔兰更习惯看到这种主张。”
对于一位英国内政大臣来说,这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尤其是一位保守党人。北爱尔兰的大多数游行都是由保守党的传统盟友、亲英联合主义者领导的,而不是爱尔兰共和党人。要么是布雷弗曼不明白这一点,要么是她在兜售错误信息,要么是她在改变英国政府对联合主义者抗议合法性的立场。(她的盟友后来声称,她的本意是批评共和党的游行。)后来有消息称,当首相的团队要求她在文章发表前调低调子时,她拒绝了。
当我从纪念碑走到海德公园(Hyde Park),加沙抗议活动就是在那里开始的时候,我开始看到一些引用内政大臣言论的标志。苏薇拉,这是一首爱情进行曲,读一篇。我们讨厌克鲁埃拉,另一个说。在海德公园角,一名戴头巾的妇女正在分发背后印着“我们不恨犹太人”的霓虹灯黄色背心。这是一种甜蜜的姿态,同时也引发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本应由背心来回答。
因为无法回避的事实是,亲巴勒斯坦的事业有时会变成反犹太主义。哈马斯在10月7日发动袭击后,一些左翼人士对这些暴行表示庆祝,而另一些人则为其辩解或轻描淡写,认为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抵抗”行为。许多人援引了殖民时期的语言,或者将这种情况解析为以色列白人与加沙和西岸的有色人种之间的种族冲突。(事实上,一半的以色列犹太人有中东或北非血统,许多人来自被穆斯林国家驱逐的家庭。)世界与巴勒斯坦站在一起。一个标语上写着:帝国主义者与以色列站在一起。小偷永远不会成为主人。偷来的土地上没有和平,第三个人宣称。有人甚至把这一切都挤在了一张12 × 18英寸的广告牌上:你不能让昨天的殖民者相信今天的殖民者是错的。
我刚看完一群白人大喊他们的土地是如何被穆斯林殖民的,这番话让我觉得毫无帮助。因此,在游行中广泛使用的口号“从河流到海洋,巴勒斯坦将获得自由”也是如此。许多英国和美国的犹太人,以及其他国家的犹太人,认为这是一种反犹太主义的要求,要消灭世界上唯一的犹太国家以色列。在美国,巴勒斯坦裔美国众议员拉什达·特莱布(Rashida Tlaib)因捍卫这一口号而受到谴责,而在英国,一名左翼工党议员因暗指这一口号而被停职。
Juliette Kayyem: Rashida Tlaib的煽动性语言
在海德公园的街角,我看到了极左的《社会主义工人报》(Socialist Worker)经营的一个摊位,该报的封面上就是这句话。我问其中一个卖报纸的积极分子他是如何理解这些话的。哈罗德只愿意透露自己的名字,他说自己是一个不做派的犹太人,并告诉我,他并不觉得这个口号有什么冒犯之处。“这关乎一个州,”他说。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在一个国家里是平等的。你不会在主流媒体上听到这一点。”那些以色列人会说,10月7日的袭击表明,他们在一个单独的国家并不安全?“答案是:停止谋杀巴勒斯坦人。”和朋友一起上街游行的伦敦人希琳(Shireen)也有类似的回答:“对于我认识的每个人——巴勒斯坦人、英国人、许多犹太朋友——它实际上意味着巴勒斯坦人在那片土地上的和平与正义。”
许多游行者真诚地相信,以色列是一个在加沙进行“种族灭绝”的“恐怖国家”。巴士候车亭上贴着写有被谋杀儿童的海报,一个团体的领导人拿着裹着白色寿衣的小包裹。游行者希望停火,然后再寻求政治解决方案。我问一位女士,她是否认为哈马斯也想这样做。“我不关心哈马斯,”她说。
我跟着游行队伍走了两个小时。人们带着自己的孩子,大多数人都很乐意带着现成的标语,这是最左派的补给,以参加这样的游行。(《社会主义工人报》为此场合把自己的口号翻译成了阿拉伯语。)但是,尽管你可以将“河归海”的颂歌归因于无知而非恶意,但这并不是唯一令人不安的因素。观众反映了一些仇恨的图像,包括一个标志,描绘了一个戴着大卫之星的“木偶大师”。
我追上了一个戴头巾的女人,她举着一个牌子,上面画着希特勒和内塔尼亚胡的脸,后者特意贴上了标签,以防混淆。你所做的也一样!它宣称。我问她为什么要带这个牌子,她似乎很困惑:“完全一样。他们所做的是一样的。”
她的一个朋友问我:“有什么不同吗?”
“嗯,”我说,“希特勒杀了六百万犹太人。
“你在行军吗?”她回答说。
“不,我在报道。”
那个女人把她的朋友拖走,说:“不要和记者说话。”
在回家的路上,在堤岸车站外,我遇到了另一条警戒线——两群流氓在酒吧里打架,现在被分开了。在回南伦敦的火车上,我看了一些汤米军的片段,他们最终找到了一些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者,在沃克斯豪尔桥上战斗。据伦敦警察厅(Metropolitan Police)称,有82人在附近被捕,“以防止破坏和平”。几小时后,在正式的巴勒斯坦游行结束后,一个分离出来的团体中约有150人也因投掷烟花和拒绝摘下面罩而被拘留和搜查。
自10月7日以来,英国一直感到发烧,这是3500英里外一场英国几乎没有影响力的冲突的结果。可以理解的是,自那以后,英国犹太人对反犹事件的增加感到震惊,而且反犹主义被一些通常对冒犯保持高度警惕的人所忽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抗议者至少可以停止高呼“从河流到海洋”,不管他们想要表达什么意思。
海伦·刘易斯:那些没有通过哈马斯测试的进步人士
伊斯兰恐惧症也有所增加,因为极右翼抓住这场冲突,提出穆斯林不属于英国的观点。甚至一些为主流右翼媒体撰稿的评论员也在玩弄这个想法;《观察家》的道格拉斯·默里告诉美国播客主持人戴夫·鲁宾,苏格兰首席部长哈姆扎·优素福是穆斯林,他的姻亲最近才离开加沙,他并不关心苏格兰。相反,根据默里的说法,优素福的社交媒体帖子显示他是“加沙的第一部长”,并且是一个“渗透”了英国政治的人。
在这个火药桶中,人们发现政客们有所欠缺。布雷弗曼对警方的行为进行了预先判断,并指责他们有偏见,这使警方的任务变得更加困难。她现在或许可以有效地反思一下,数万名支持巴勒斯坦的和平示威者参加了游行,而煽动者可能从她的话中得到了鼓励,导致纪念碑前出现了丑陋的场面。
看完两场抗议后,我意识到了一些事情。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我们的社交媒体上,英国都充斥着决斗的象征。汤米的许多军队都举着装饰着罂粟花的大横幅,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爱国主义的象征,而海德公园里到处都是巴勒斯坦国旗的红、黑、绿。每个符号在另一个事件中看起来都不合适。一些人认为红罂粟是帝国主义对英国的一种强制爱国主义的图腾,而不是一种中立的纪念战争死难者的方式。另一方面,挥舞着巴勒斯坦国旗的是真正的反犹主义者——他们说“犹太复国主义者”,其实是指“犹太人”——被认为是对10月7日事件的无情漠视。
在双方极端分子相互依存的情况下,这些理解上的分歧将难以弥合。英国应该是一个罂粟和巴勒斯坦国旗可以共存的国家。
相关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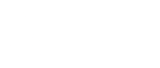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