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萨满如何帮助他人在现代世界找到治愈和意义

在举行仪式的前一天,来自世界各地的40多人将聚集在哥本哈根,体验由韩裔美国萨满巫师海伦娜·索霍尔姆(46岁)主持的萨满仪式。
在想要更多地了解萨满教时,我看到了海伦娜的作品。现在我们一起在丹麦的新西兰,还有将在仪式上陪伴海伦娜的韩国传统音乐家金东源(58岁)。
当我们到达海滩时,天还是有点阴,大地被厚厚的白色的雪毯冻住了。东元望着窗外说:“大海欢迎我们。”我对海伦娜说:“对不起,我想在旅行前多做一些关于萨满教的研究,但我没有时间。”她回答说:“奥林,这是一种殖民主义看待萨满教的方式。你通过体验来了解它。”海伦娜和东元在仪式前向五个方向鞠躬。中心是第五个方向。
在农业社会时期,在收获季节,村民们会演奏自己特有的音乐,游行到邻近的村庄,帮助彼此工作。据Dong-Won说,“在稻田里干活是很辛苦的工作,所以唱歌和打鼓是必不可少的。随着分娩越来越困难,鼓声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刺激。那是我第一次在音乐中了解到同理心的概念。”他开始演奏一个有200年历史的锣,突然间,天空豁然开朗。
现代治疗
海伦娜是一名超个人心理学家,也是一名萨满巫师。在她的作品中,她将西方心理学理论与本土知识体系相结合,以促进现代科技发达社会的治疗和发展。
她说,在2018年加入萨满后不久,她看到了一个异象,看到了被西方国家收养的韩国人的祖先,渴望与他们的后代联系。她说,她相信“清理和尊重祖先的能量是通过恢复土著思想来实现的,这可以加深一个人与自我、他人和土地的联系”,因此她为被收养者和其他想要与祖先联系的人提供仪式和朝圣。
海伦娜嫁给了一个丹麦人,在丹麦发展了许多关系。她说,她的村庄现在是全球化的,“所以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我的理念是我们要创造神圣的空间。”
参与者
参加在哥本哈根举行的仪式的被收养者中,有代表丹麦韩国被收养者协会“Korea Klubben”带来内脏仪式献金的詹尼·容·韦斯特曼(45岁)。她是第一批为调查韩国儿童国际收养背后的腐败行为而收集信息的人之一。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韩国儿童国际收养的产业规模达10亿美元。
2001年,珍妮和一名韩国社工一起寻找一个家庭。她了解到,被收养者通常不会得到完整的档案。尽管最初的记录显示她被遗弃了,但珍妮还是找到了她的亲生父母。在见到亲生父亲多年后,她与一名私家侦探合作,找到了亲生母亲。
在韩国被领养的丹麦籍韩国人麦顺英?vlisen(41岁)第一次听到了韩国传统音乐。“我听到了痛苦的声音,人民的历史和过去,作为一个国家,就像,那是我的声音。我的声音是韩语。现在,她与她的乐队“Meejah”(意为“媒介”)一起将韩国传统民乐和萨满教融入到音乐实践中。在找到她的亲生父母时,Mai说:“我只是为它腾出空间,为它打开空间,让它走到一起,如果它想要的话。”
在许多其他国家,包括曾经被丹麦殖民的格陵兰岛,不道德和非法的收养做法是一个系统性问题。Kalánguak Absalonsen, 53岁,她的父亲在她3岁时自杀,她被从亲生家庭带走。她的母亲签署了收养文件,却没有意识到她放弃了自己的孩子,因为在因纽特文化中,没有关于收养的词或概念,她认为,“当雪消失时,他们会回来的。”但是她的孩子们没有回来。她给Kalánguak寄了信,但她的养母把信藏了起来。当我问Kalánguak她对格陵兰岛的记忆时,她谈到了雪的声音:“当它真的很冷的时候,它有一种特殊的声音。”
46岁的韩裔美国作家汤姆·平(Tom Pyun)是海伦娜的客户,他从洛杉矶飞来参加颁奖典礼。他的父亲在他13岁时去世,他的母亲在2021年因COVID-19突然去世。当他看到海伦娜的作品时,他一直在寻找其他治疗方法:“没有机会真正说再见或得到任何结束,我想也许一个萨满可以帮助我找到结束——那些本可以说或应该说的话。”
44岁的安妮-玛丽·汉森(Anne-Marie Hansen)是丹麦的一名设计教授,她在丹麦的家族血统可以追溯到15世纪。她对仪式很好奇,并发现了更多她与北欧异教文化的联系。她说,她希望这个仪式能帮助她恢复传统知识,恢复文化记忆,并与自然建立联系。
仪式
在仪式当天,许多参与者穿着来自他们本土文化的东西,以帮助他们与祖先联系起来。随着他们的慢慢到来,许多人在祖先的祭坛上添加了特殊的物品和纪念品。红、蓝、白、黄、绿四色织物,分别代表五个方向。每个人都挑选了几块撕破的布料,随着东元和从韩国传统中传承下来的西方巫师亨德里克杰·朗格(Hendrikje Lange)有节奏的鼓声,缓慢地走向仪式场地baneggarden入口处的一棵树。根据海伦娜的说法,“因为那里有很多来自不同文化的人,我们需要某种活动把我们聚集在一起,这样每个人都已经在他们的无意识层面上做好了准备,从而触发我们内心深处的一些东西。”
海伦娜用白色织物创造了一个圆圈,邀请不同群体的人进来,从被收养的人开始。他们开始跳跃,进入一种恍惚状态。有母亲的渴望、深深的痛苦和悔恨的哭声。在土著的圈子里,能量和空气转移。当海伦娜听到“阿雅,阿雅”这句话时,来自格陵兰岛的因纽特电影人阿克
·汉森(akhansen)突然唱起了歌。对于欧洲组,海伦娜很难通过,所以她要求其他参与者将他们的能量传递给这个组。许多人闭上眼睛,摆好手。“这里有很多堵塞。有很多男性的能量,”海伦娜说。最后,一小群散居在外的成员进入了白色圈子,并开始谈论破碎的梦想。最后,所有人都跳在一起,海伦娜为每个人祝福。仪式之后是一场讨论,我们知道ak
唱的那首歌是她第一次唱。这是一首ak
祖先的歌。
仪式结束后的第二天,我问参与者他们是如何处理自己的经历的。Kalánguak谈到了被收养者圈子里的母性能量:“听到妈妈们在我们身后喊‘没事’,感觉很好。我在这里。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对我来说,这是一种解脱。我这辈子都听人说我妈妈照顾不了我。但事实并非如此。海伦娜打开了我的心,用爱接纳了我的母亲。”
“我会花很长时间考虑这个仪式,”麦顺杨(Mai Soon Young)说。“这让我感到并不孤单。”
本报道得到了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劳伦·布朗奖学金的支持。
Arin Yoon是堪萨斯城的韩裔美国摄影师。在她的网站arinyoon.com和她的Instagram @arinyoon上可以看到更多她的作品。
图片编辑:Grace Widyatmadja。文本编辑:Zachary Thompson。
相关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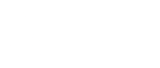
最新评论